關(guān)于死刑的適用標(biāo)準(zhǔn),應(yīng)結(jié)合《公約》的規(guī)定和中國現(xiàn)行刑法的規(guī)定,從源頭上把死刑的適用范圍控制在最低限度。有學(xué)者建議將“最嚴(yán)重犯罪”標(biāo)準(zhǔn)與“極其嚴(yán)重犯罪”標(biāo)準(zhǔn)相結(jié)合,前者是立法甄別,后者是司法限制。上海律師就來回答一下相關(guān)的情況。

筆者贊同這一觀點(diǎn),認(rèn)為這兩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應(yīng)該在立法和司法環(huán)節(jié)發(fā)揮限制死刑的作用。即應(yīng)當(dāng)在刑法中規(guī)定死刑適用于“罪行極其嚴(yán)重的最嚴(yán)重的犯罪”,對(duì)犯罪的性質(zhì)和程度進(jìn)行雙重限制。這樣,一方面可以引導(dǎo)立法者在立法中慎重考慮死刑的適用范圍,慎重考慮哪些罪名可以配置死刑,哪些罪名不需要配置死刑,只有最嚴(yán)重的犯罪才可以配置死刑。
另一方面,也可以指導(dǎo)司法實(shí)踐,即法官首先要判斷一個(gè)案件是否屬于最嚴(yán)重的犯罪,如果屬于最嚴(yán)重的犯罪,那么就可以考慮使用死刑。如果行為本身不是最嚴(yán)重的罪行,即使罪行極其嚴(yán)重,也不能適用死刑。經(jīng)過立法和司法的雙重判斷,死刑的適用標(biāo)準(zhǔn)可以更加嚴(yán)格,死刑的適用也可以更加慎重。
為了加快推進(jìn)死刑改革,立法上應(yīng)大幅度地廢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。首先,雖然非暴力犯罪也具有嚴(yán)重的社會(huì)危害性,不具有嚴(yán)重社會(huì)危害性就不會(huì)被規(guī)定為犯罪,立法者在設(shè)置之初更不會(huì)為其配置極刑,但是,隨著人權(quán)觀念的提高,人們已逐漸認(rèn)識(shí)到其他任何權(quán)利都是無法與生命權(quán)相比的,通過剝奪生命權(quán)來懲罰非暴力犯罪不具有等價(jià)性,不符合刑罰的報(bào)應(yīng)目的。
其次,對(duì)實(shí)施非暴力犯罪的罪犯適用死刑,可以通過從肉體上消滅徹底預(yù)防其再次犯罪,但是否有必要呢?死刑的威懾作用在非暴力犯罪尤其是非暴力的經(jīng)濟(jì)犯罪中究竟有多大?這些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尤其是對(duì)于貪利型的犯罪而言,完全沒有必要?jiǎng)佑盟佬倘ヮA(yù)防犯罪,動(dòng)用死刑的成本過高,可以通過無期徒刑、有期徒刑對(duì)其教育改造來預(yù)防其再次犯罪,這也正是刑法謙抑性的要求。
更進(jìn)一步分析,對(duì)于此類犯罪,即使動(dòng)用死刑可能也無法實(shí)現(xiàn)一般預(yù)防的刑罰目的,通過社會(huì)綜合治理的方式預(yù)防此類犯罪往往會(huì)事半功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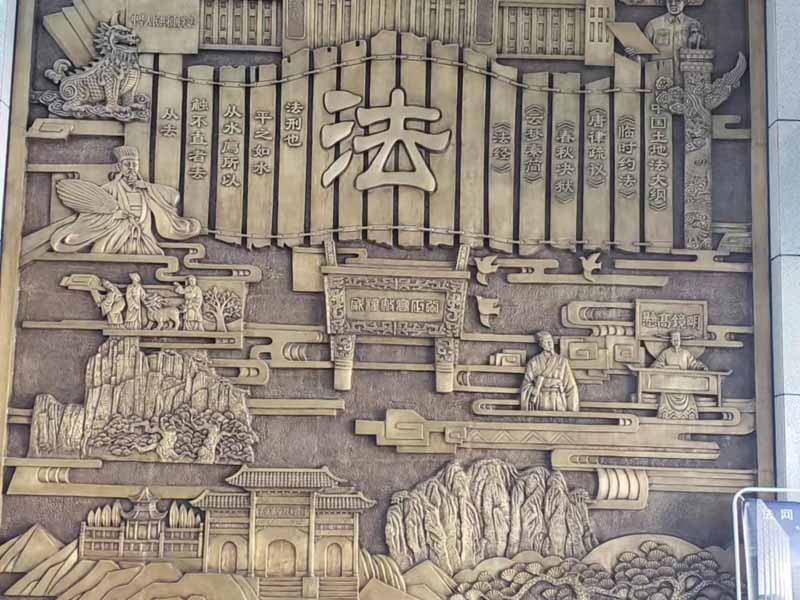
再次,廢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也是為公眾較易接受的。雖然報(bào)應(yīng)觀念在我國民眾心理中已經(jīng)根深蒂固,完全廢除死刑與公民的價(jià)值觀相矛盾,但民眾普遍難以接受的是“殺人不償命”,而對(duì)于非暴力犯罪廢除死刑,本身的抵觸情緒就小很多,而且,隨著經(jīng)濟(jì)的發(fā)展,社會(huì)的進(jìn)步,公民權(quán)利意識(shí)的提高,民眾已經(jīng)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,進(jìn)一步加快廢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所面臨的民眾觀念上的阻力不會(huì)太大。
最后,實(shí)踐證明,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大量廢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后,沒有引起社會(huì)動(dòng)蕩,沒有引起公眾心理恐慌,社會(huì)治安狀況沒有明顯惡化。
“2011年出臺(tái)的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取消了13個(gè)經(jīng)濟(jì)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以來,中國社會(huì)治安形勢總體穩(wěn)定可控,一些嚴(yán)重犯罪穩(wěn)中有降。”這就為《刑法修正案(九)》以及今后大規(guī)模廢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提供了現(xiàn)實(shí)基礎(chǔ)。在廢除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同時(shí),同步廢除暴力犯罪死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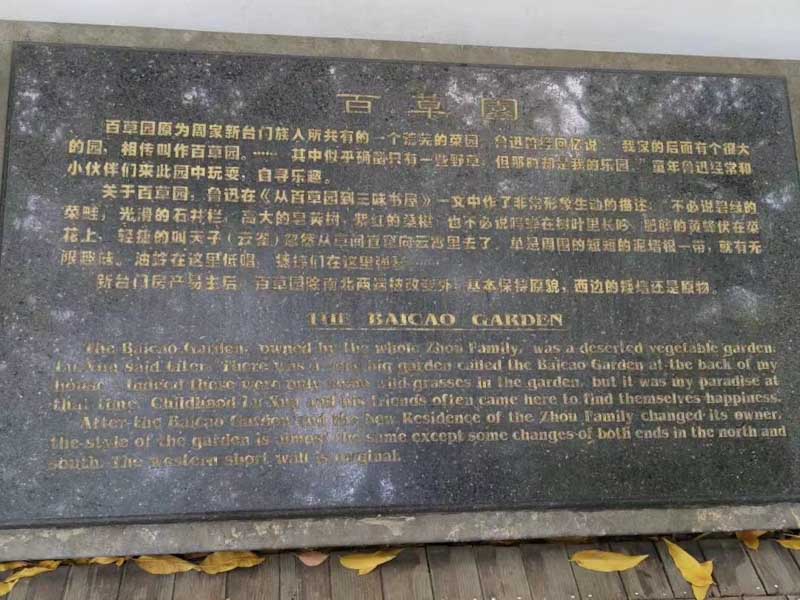
《刑法修正案(九)》已經(jīng)邁出了中國廢除暴力活動(dòng)犯罪死刑的第一步。上海律師認(rèn)為,在立法上可以不斷加快發(fā)展推進(jìn)國家廢除暴力違法犯罪死刑的步伐,尤其是非致命暴力信息犯罪的死刑廢除一些問題,應(yīng)該學(xué)習(xí)成為企業(yè)今后我國死刑改革的重點(diǎn)。按照這種暴力文化程度的不同,暴力犯罪人員可以主要分為一個(gè)致命性暴力犯罪和非致命性暴力犯罪。






 網(wǎng)站首頁
網(wǎng)站首頁  在線咨詢
在線咨詢  電話咨詢
電話咨詢